《二泉映月》行--采访作曲家汪成用(上)
打印机版 | 【投稿/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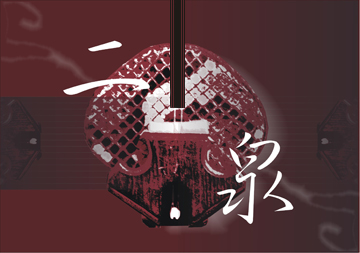 |
杨晓玫:《二泉映月》是广大观众所熟悉的一首中国民间二胡曲,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沉浮,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经久不衰。伴随着《二泉映月》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艺术家的命运又是如何呐?请您收看我们的专题片《二泉映月》。
一九九八年由杨逢时指挥的芝加哥东西方音乐艺术团演奏的西乐协奏二胡曲《二泉映月》上演了。西乐协奏的《二泉映月》并不多见,且伴奏部份单调乏味,当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准备上演西乐协奏《二泉映月》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艺术总监杨逢时就在离演出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候决定改写伴奏部份,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作曲家汪成用的身上,汪成用夜以继日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伴奏部份的谱曲。经改写后《二泉映月》的演出效果大不一样,伴奏部份更加浑厚充实而且与二胡部份遥相呼应,赋予了音乐更加丰富的内涵。
谈到改写伴奏曲谱的感想时却道出了音乐家与艺术的一场缘份,以及在中国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年代在传统艺术和革命现代文化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艺术家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一个有天份的艺术家也只能是望琴心叹可望而不可及,因此都纷纷玩起了价格比较低廉的二胡和笛子,就这样酷爱音乐的汪成用也玩起了二胡。
汪成用:西洋乐器都很贵,我记得当时的小提琴大概要二十块,二十块现在没什么但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二胡呐顶多两块、一块多,笛子几毛钱,所以当时要学音乐的话只能玩这些东西,我就学了二胡。
杨晓玫:玩起了二胡当然也就离不开经典曲目《二泉映月》。
汪成用:小时候学二胡,长大了以后进了音乐学院,学习了中国的民间音乐才知道《二泉映月》是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个经典,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民间音乐的瑰宝。我想她的这几个特点可以提一提:一个是《二泉映月》是少有的由中国作曲家作曲的中国音乐,当然阿炳不是作曲家这个等一下再提。(由中国作曲家作曲的中国音乐)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呐?因为一个民族的音乐如果想在世界乐坛上占一席之地的话,没有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而仅靠民族的音乐遗产是不够的,它形不成一个音乐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德国音乐那自然想到的是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这样的作曲家,如果仅仅有德国民歌那么就形不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德国音乐。象俄国音乐、法国音乐都是有一大批非常成熟的、非常有作为的作曲家。那么中国的音乐呐,老实讲没有作曲家,阿炳本身也不是个作曲家,他是个民间艺人。但是《二泉映月》是少有的一首由音乐家作曲的作品,这个很难得。象其他的一些如《平湖秋月》、《阳关三叠》等这样的一些组曲都是留下的传统音乐,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作曲的。所以从作曲角度来讲这些就不象《二泉映月》这么完整,这是其一;其二呐,《二泉映月》实际上非常接近于西方的“无标题音乐”。那么有人可能不同意,《二泉映月》都说是描写无锡惠山的优美景致,为什么说是无标题音乐呐?但实际上《二泉映月》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标题。直到杨荫藒教授去找到瞎子阿炳请他录音。录下《二泉映月》的时候当时还不知道《二泉映月》叫什么。录完了以后杨荫藒问阿炳这首曲子叫什么?据说当时阿炳沉思良久最后说:“就叫二泉印月吧。”他当时说的“印”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辉映的“映”而是“印”。据说另外一位民族音乐大师曹安和,她是杨荫藒的表妹,当时也在录音现场,当时就背了两句苏东坡的诗: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当时大家都觉得有月有
泉意境非常好。经过杨荫藒和当时另外一位民族音乐大师梁天授共同商量把这个“印”改成了辉映的“映”。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二泉映月》在创作的过程中没有标题,她只不过是阿炳心中的一种感受而已。那么无标题音乐和标题音乐相差很远,无标题音乐具有更宽广的内涵。比如说你今天听和明天听两天的心情不一样,可能会听出不同的体会,就是说无标题音乐提供给听众一种极大的想象空间,这个在中国音乐中比较少见。
再有一点《二泉映月》自从阿炳录音以后,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马思聪非常震动、非常喜欢,曾经有意请阿炳到中央音乐学院来任课,甚至于当教授。但是因为当时阿炳已经病的很严重,第二年就辞世了所以没有实现。但是这首曲子半个世纪以来受到了中国听众、中国的专业音乐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极大的欢迎,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反响。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叫做死?死就是不能再听《二泉映月》了。”当然这是一种感情话了,但是说明了大家对《二泉映月》有多喜欢。
我记得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吴祖强把《二泉映月》改编成弦乐曲,但是没有二胡就是传统的西方弦乐。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乐团也很少,我记得是西德的斯图加特弦乐团到中国演出以后演了这首曲子,演奏的时候好多老先生老泪纵横,很感动。以后著名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也指挥过这首曲子也是非常感动。他甚至说:“《二泉映月》应该跪下来听。”可见这首曲子对于世界和中国震动都很大,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我想这也是我改编她的一种动力。
杨晓玫:当时你怎么想起要把《二泉映月》改编成协奏曲?
汪成用:一九九八年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准备开音乐会的时候,刚开始并没有想创作这个《二泉映月》,当时我们挑选了几个西方弦乐和中国二胡结合的版本排练,排练了以后都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我们挑的版本没有把《二泉映月》的意境表现出来。既然没有挑到合适的就决定自己写一个。当然这个写并不是把《二泉映月》写了,《二泉映月》是个经典,是没办法重写的。我用的是杨荫藒教授记谱的原版,二胡部份一点都没有改,主要是在弦乐协奏上作了文章。
杨晓玫:当时听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怎么敢接下这个任务?
汪成用:两个星期,我自己对《二泉映月》非常喜欢,从小是听着她长大的,所以说对她很了解。其实在下笔之前到底应该怎么写心理已经都有数,所以花了大概一个星期写出来,然后再一个星期排练。
杨晓玫:文化大革命期间以《二泉映月》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及文化几近夭折,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样板戏”(注)为代表的共产党文化。一九六八年汪成用随着第一批“上山下乡”的洪流从北京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一次兵团表演舞剧《白毛女》时,由于缺少低音大提琴伴奏会拉二胡的汪成用派上了用场,他用破鼓制作了一个革胡拉了起来,由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
汪成用:当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演<白毛女>又没有低音乐器,所以就拿鼓做了一个革胡,因为鼓皮很厚拉起来震动不了所以就特别难听,但是弹起来很不错,我就是从那个开始玩儿,慢慢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后来“革”了两年以后,音乐学院来招生的时候我已经会拉大提琴了,因为从革胡慢慢学会大提琴就进入了音乐学院,这就是我学音乐的经历。可以说是由于最初对象《二泉映月》这样民族音乐的热爱,最后又鬼使神差地和样板戏搭了个缘,这样使我走上了音乐道路。可以说是在这种民族音乐和革命样板戏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在这种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杨晓玫:在中国传统艺术和共产党革命现代文化交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艺术家如何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传统呐?请在下次节目中继续收看我们的专题片《二泉映月》。
注:样板戏可说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唯一的舞台艺术,它不但能反映文革的思想主张,当时更成为宣传工具,以不同方式,渗透全中国,形成“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奇特现象。来源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等连串的运动展开,中国戏曲界亦备受批评,以为传统戏都是宣扬封建,主张多演现代戏,排斥传统戏。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当中《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等被列为为优秀剧目,各地遂纷纷上演这些以工农兵革命为主线的现代革命戏,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则渐次在舞台消失。文革展开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1966年11月28日宣布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沙家滨》、《红灯记》、《海港》和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滨》等八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
在文革的十年,样板戏垄断了整个戏曲舞台,各地京剧团都搬演样板戏,其余地方剧种也把样板戏移植演出。样板戏除了以戏剧和舞剧的方式在全国公演外,还制成彩色电影、电视纪录片、广播剧、唱片、中小学语文课本,甚至发行剧本、曲谱、挂图、年历、明信片、字帖、画片等等,无孔不入,使样板戏很快由舞台进占八亿人民的精神领域,形成了“人人都唱革命样板戏”、“学唱样板戏,争做革命人”的局面。
发稿:2005年2月6日
更新:2005年2月6日



